严元章藏书0099
《多元社会中的教育发展:马来西亚案例研究》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Plural Society: A Malaysian Case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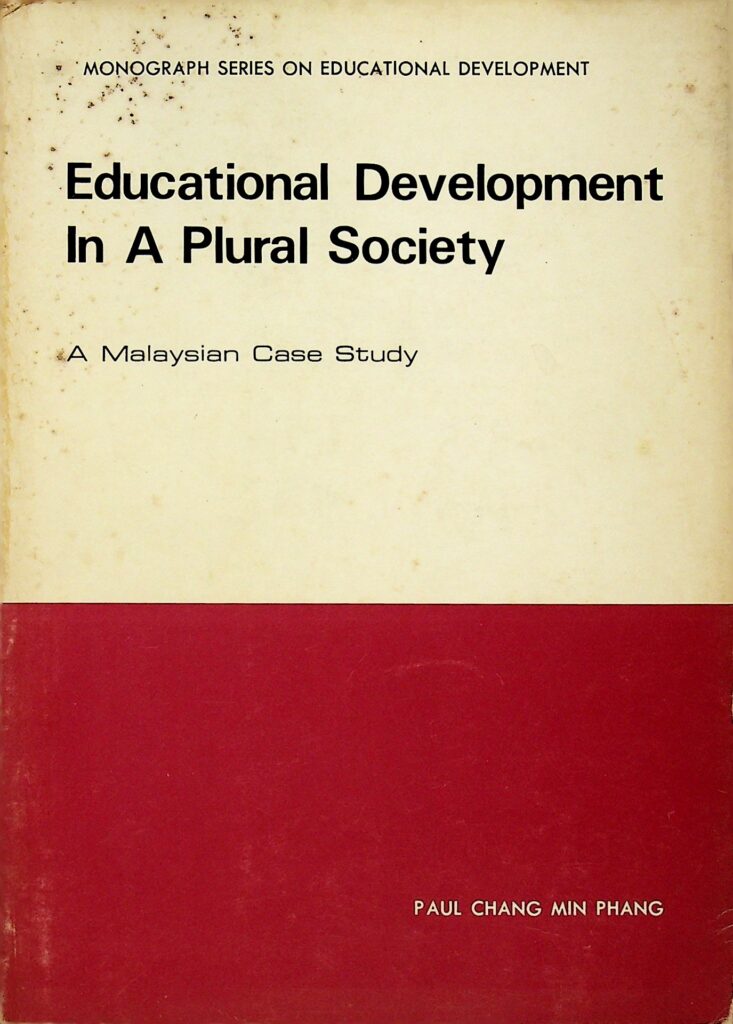
Paul
Chang Min Phang 所著的《多元社会中的教育发展:马来西亚案例研究》专著系列,概述了马来西亚(当时包括新加坡和马来亚)教育系统的历史演变。文章着重探讨了殖民时期(1786年至1942年)“多元学校系统”的出现,该系统根据不同的族群和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将教育分化,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衡。随后,作者讨论了独立前夕(1945年至1957年)为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政策”所做的努力,包括巴恩斯委员会和芬–吴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旨在融合各种教育流派的立法,如《1957年教育条例》。最后,文章考察了独立后(1957年至1967年)的教育发展趋势,例如推行免费初级教育、提高入学年龄、引入综合教育系统,以及教育作为国家整合和经济发展工具的作用,特别是通过改革教师培训和设立独立的巡视机构来提升教育质量。
该专著属于“教育发展专题系列”的一部分,旨在为比较教育研究者提供关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教育发展的宝贵资料。这两个国家拥有共同的殖民遗产,都是多民族社会,面临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问题,并将教育视为民族整合与发展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仅限于西马来西亚(即马来半岛)的教育发展情况。作者的三个主要目标是:
- 追溯从 1786 年到 1967 年,多元学校体系如何演变为旨在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融合和经济发展的国家体系。
- 确定并讨论实施国家教育政策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 指出几个主要的教育发展趋势。
作者将多元社会定义为“社区的不同部分并存但在同一政治单元内分别生活”。多元学校体系则意味着两种或多种学校体系并存,但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包括教学语言媒介、拨款和师资培训设施的提供,以及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详细章节书评
第一部分 早期发展时期:1786–1942
第 1 章 多元社会的演变
本章阐述了马来亚多元社会的形成背景。英属马来亚的行政政策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英国通过条约获得了海峡殖民地(槟城、新加坡、马六甲)以及马来州属的控制权。英国的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锡矿和橡胶业,这些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由于本土马来人不愿从事矿场和种植园的有偿工作,英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劳工。
- 华人移民: 大量华人移民涌入,至 1941 年,华人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 44%。
- 印度人移民: 主要招募泰米尔人,从事橡胶种植园、道路和铁路建设。至 1941 年,印度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14%。 这种不受限制的移民形成了多元社会,人口激增,改变了国家的人口结构。由于文化差异(如宗教、饮食禁忌),社会融合变得困难,社区倾向于分开居住,几乎没有通婚。鲁珀特·爱默生(Rupert Emerson)因此将马来亚描述为“弗尼瓦尔多元社会的典型代表”。
第 2 章 多元学校体系的发展
多元学校体系的发展主要受三个因素驱动:多种族人口结构、志愿机构的努力(教会、社群利益)以及缺乏一致的教育政策。英国早期行政侧重于经济,认为对马来人的教育义务只是提供一种初级教育,旨在让他们继续从事农渔业。政府不认为有义务为移民子女提供母语教育。
a) 马来学校: 英国承诺根据条约保护和照顾马来人,提供免费的四年制母语初级教育。早期教育由可兰经学校发展而来。经过斯金纳(A.W. Skinner)的改革,世俗教育逐渐被接受。威尔金森(R.J.
Wilkinson)和温斯泰特(R.O. Winstedt)推动了教育改进,包括引入罗马化马来文(Rumi)和侧重实用技能的课程(如园艺、手工)。在数量上,马来学校在 1942 年拥有最高的入学率。但在质量上,校舍简陋,缺乏教材,师资培训不足,没有中学教育设施,限制了马来人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 b) 华文学校: 发展主要依赖华人社群的努力和对学习的传统重视。早期以不同方言授课,课程老式,环境恶劣。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现代华文学校兴起,但其内容和形式完全是中国化的,与马来亚的政治文化背景脱节。虽然政府后来提供了补助和监督,但教科书仍然以中国为中心。设施差、教师工资低,毕业生缺乏公认资格,导致失业和不满,成为共产党招募的温床。 c) 印度学校: 早期由私人机构设立。1912 年的《劳工法典》要求拥有 10 名学龄儿童的种植园必须提供学校。印度学校主要服务于种植园劳工子女,课程通常为四年,具有乡村倾向。然而,印度学校像马来学校一样,是“死胡同”(cul-de-sac),除了为种植园提供廉价劳动力外,对学生帮助不大。 d) 英文学校: 主要由传教士团体和慈善组织创立(如槟城免费学校,1816 年)。政府也提供财政支持。课程高度学术化,为剑桥海外学校证书考试做准备。政府对英文教育的政策是限制性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昂,以及担心培养出大量失业、不满的西方教育青年(“失败的文学学士”)。英文学校集中在城镇,形成了受英文教育的“精英阶层”,并成为不同种族儿童共同学习的唯一场所。
第 3 章 教育发展的其他方面
a) 职业和技术教育: 发展缓慢。尽管早在 19 世纪初就有相关建议,但直到 1918 年“莱蒙委员会”的报告才提出了建立技工学校、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的具体建议。切斯曼报告(1938)和麦克莱恩委员会(1939)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建议将手工艺纳入课程,并提升吉隆坡技术学校的地位。然而,缺乏科学和手工艺教师的培训,成为扩大职业教育的严重障碍。 b) 师资培训: 缺乏一个连贯的体系,培训方案因学校体系和语言媒介而异。包括:针对中小学的“师范班”(Normal Classes);为马来学校培训教师的丹戎马林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学院和马六甲女子师范学院;以及为中等教育培训教师的拉弗尔斯学院(Raffles College)。 c) 高等教育: 在 1942 年前,高等教育机构只有两所,均位于新加坡,使用英语教学: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1905 年)和拉弗尔斯学院(1928 年,文理科)。学生入学需要通过剑桥海外学校证书考试。在拉弗尔斯学院,华人占学生总数的 58%,印度人占 22%,而马来人仅占 9%,显示了多元学校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部分 独立前时期:1945–1957
第 4 章 寻求国家教育政策
战后政治变化迅速,英国致力于让马来亚实现独立。教育改革尝试与政治发展阶段相平行。 b) 切斯曼计划(1945–1949): 建议提供免费母语初等教育(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英文),并将英文教学扩展到所有小学。该计划因将母语学校扩展到中学层面,被认为可能加剧和延续社群差异。 c) 巴恩斯委员会报告(1951)和芬恩–吴报告(1951):
- 巴恩斯报告: 建议将现有学校逐步转型为国民学校,使用英文和马来文双语教学。其核心原则是:只要不同社区的儿童在独立的学校接受教育,就难以实现社会融合和民族团结。报告甚至将接受国民学校体系与对国家的忠诚联系起来。这立即引起了非马来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华人,他们认为这是对其语言文化的威胁。
-
芬恩–吴报告: 为安抚华人而设立。报告强调文化整合不可能人为快速创造,并认为大多数华人愿意学习三种语言。其观点与巴恩斯委员会形成鲜明对比。 d) 1956 年教育委员会报告和 1957 年教育法令: 1952 年的《教育法令》在和解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设立了两种国民学校(马来文媒介和英文媒介),并允许在有需求时提供华文和泰米尔文教学。但实施受阻于师资短缺和财政限制。 1955 年,联盟党上台后,任命了以 Dato Abdul
Razak(敦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体系,强调教育是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工具。主要建议包括: - 所有学校采用共同核心课程,灌输马来亚观念。
- 建立统一的教师服务体系。
- 将现有小学转为标准学校(马来文媒介)和标准型学校(其他媒介),所有教师接受相似培训。
- 马来文和英文(如果不是教学媒介)在所有学校中成为必修科目。
-
建立一种面向所有种族的国家中学,采用灵活课程,允许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但考试将标准化。
该报告于 1957 年通过《教育法令》获得法律地位,标志着独立马来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 e) 高等教育: 1948 年卡尔–桑德斯委员会报告建议将两所学院合并。1949 年,马来亚大学正式成立,成为唯一的学位授予机构。
第三部分 独立后时期:1957–1967
第 5 章 1960 年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和 1961 年教育法令
1960 年的报告确认了 1957 年教育政策的基本成功(如引入共同课程、扩大师资培训)。
- 免费初等教育: 1962 年实施,导致英文小学入学率明显增加,因为许多家长认为英文教育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 提高离校年龄至 15 岁: 目标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九年教育,解决 13 岁儿童太年轻无法合法就业的问题。为此建议设立三年制后初等课程(Post-primary course),但由于其不颁发任何公认资格,该计划极不受欢迎,于 1965 年被废除。
- 公共考试的语言媒介: 建议中学公共考试仅以马来文和英文这两种官方语言进行。目的是为了民族团结,尽管教育检讨委员会承认这违反了“用一种语言教学,用另一种语言考试是不合理的”原则。
- 暂停地方教育当局: 发现地方教育当局(LEA)未能有效地筹集资金,或促进地方对初等教育的参与。在某些地区,还存在地方政治干预学校管理和教师任命的问题。因此,委员会建议暂停该制度。
第 6 章 综合教育体系的引入
1965 年,综合学校体系(Comprehensive School
system)引入。废除了中学入学选拔考试,所有完成六年小学的学生都被录取进入初中一年级或预备班(Remove
Classes)。
- 课程结构: 提供了三年非选拔性的、统一的、综合性和职业预备性的教育。学生必须学习一组“核心科目”和至少一门“选修实践科目”(如工业艺术、家政)。
- 目标: 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旨在为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所需的熟练劳动力。同时也实现了将离校年龄提高到 15 岁的目标,并允许学生在接受九年教育后,根据才能决定未来的职业。
- 挑战: 实施这一大规模计划给国家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需要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并导致几乎所有初中都实施了双班制。
第 7 章 教师的供给和培训问题
战后教育扩张惊人(1946 年至 1966 年,入学人数增长超过 500%)。
- 统一服务: 拉萨委员会建议建立统一的教师服务体系和薪资等级。
- 培训重组: 取消了多样的培训计划。小学教师培训要求学生必须学习马来文或英文作为第二语言。中学教师培训则由马来亚大学和全日制住宿学院负责。
- 专业化: 引入了综合师资培训计划,使各个师范学院在特定领域(如槟城:数学和科学;吉隆坡:技术和职业科目)进行专业化培训。
- 应对综合教育: 1965 年实施综合教育后,教师需求激增。政府采取了两年制“三明治”课程(即区域中心兼职授课,假期全日制培训)来解决燃眉之急。该计划的成功体现在未受训教师比例显著下降(从 1953 年的 80%以上降至 1966 年的 40%以下)。
第 8 章 独立学校督学处的设立
巴恩斯委员会于 1951 年建议设立独立督学处,以确保在行政人员行政职责过重的情况下,教育标准得以维持和发展。
- 职能: 联邦督学处于 1956 年设立。其职责主要是提供专业建议,并向教育部长报告检查结果,但无权向学校发布指令。这取代了战前各语言部门互相隔离的督学体系。
- 挑战与调整: 督学处早期面临招聘困难和与行政官员关系紧张的问题。1960 年教育检讨委员会要求督学处与教育部更紧密地合作。随后,督学处的重点从正式检查转向学校访问和组织短期在职培训课程。尽管该部门人手不足,但它在复杂的多语种教育体系中,通过首席督学的卓越领导,致力于确保教育质量。
第 9 章 几个主要发展趋势
- 教育质量: 马来西亚在加速扩张中,努力平衡数量增长与质量维持。
- 成人教育和扫盲: 采取多部门合作方式(如国家和乡村发展部、农业部),旨在消除文盲和培训技能,缩小城乡差距。
- 课程规划与发展: 趋势是从短期的、临时性的课程委员会(1956 年、1964 年)转向永久性的中央课程委员会(1967 年推荐),以实现更系统的长期规划和评估。
- 马来文作为教学媒介的使用: 中学马来文媒介教育迅速扩大。然而,部长们担心只懂马来文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可能形成“马来教育的失业者”群体,导致社会动荡。这促使教育部长敦促在马来文学校中投入更多时间教授英文。
- 教育规划与国家发展: 教育规划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并与高层次人力需求紧密联系。教育现在被视为国家总体发展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投资。
总结性评价
专著的结论指出,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已经从早期殖民地时期被视为“消费者负债”(consumer’s
liability)发展为被接受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投资。作者强调,教育发展在多元社会中具有分裂性和统一性的双重影响。教育本身是中立的,它最终是分裂还是统一,取决于领导者如何设计和利用它。该书清晰地描绘了马来西亚如何试图通过教育来纠正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失衡,最终实现“民族团结和公正社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