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97
裴斯泰洛齐:教育改革家(1746-1827)
Pestalozzi:Educational Reformer 1746-1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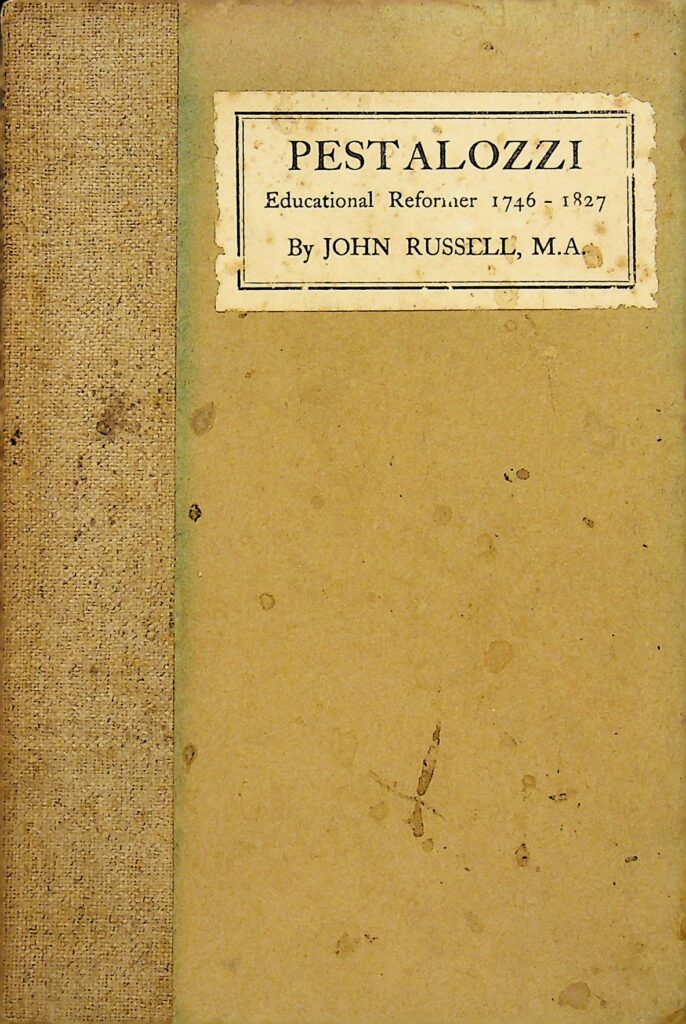
本书概述了瑞士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 1746-1827)的生平和工作,主要依据德·甘普斯(De Guimps)的传记,并由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撰写。书中详细记述了裴斯泰洛齐从早年在家受到的影响、失败的农业和慈善实验,到他创立并运营教育机构的经历,如在诺伊霍夫(Neuhof)的早期尝试、在斯坦茨(Stanz)担任孤儿之父、以及在布格多夫(Burgdorf)和伊韦尔东(Yverdon)城堡创办学校。文本的核心在于阐述裴斯泰洛齐的基本教育原则,即教育应以感官印象(sense-impression)为基础,遵循儿童心智发展的自然规律,强调家庭训练的重要性,并致力于通过全民教育来提升贫困民众的道德和物质生活水平。最后,文本讨论了其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方法)的影响和持久价值。
本书是关于瑞士著名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生平与工作的简短记述。作者约翰·罗素承认,这主要是他翻译的德·金普斯男爵(Baron Roger de Guimps)的《裴斯泰洛齐生平与著作》的摘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裴斯泰洛齐毕生的目标是提升民众,他将教育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
第一部分:苏黎世(1746-1769)和纽霍夫(1769-1798)
早期影响、大学学习与政治抱负(1746-1769)
裴斯泰洛齐于1746年出生于苏黎世,是意大利难民后裔。他五岁丧父,母亲和忠仆巴贝利(Babeli)在极其严格的节俭下抚养他长大。这种早期的家庭生活对他后来关于家庭在健全教育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童年时期相对孤僻,缺乏身体活动,导致性格有些害羞和笨拙。但他在祖父(一位乡村牧师)的陪伴下,接触了自然和田野工作,并首次萌生了减轻穷人苦难的强烈愿望。
在苏黎世大学学习神学期间(15岁开始),他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位热心的门徒和社会改革家。他最初希望成为一名乡村牧师,后转学法律,但因积极参与政治社团并撰写抨击政府的匿名小册子(例如在周报《纪念》Memorial上发表文章)而受到政府压制。他最终放弃了法律和公职的希望,转而寻求通过教育来克服民众的无知与罪恶,以改善他们的境况。
纽霍夫的农业和慈善实验(1769-1798)
裴斯泰洛齐将注意力转向科学农业。他与安娜·舒尔特斯(Anna Schulthess)订婚并于1769年结婚,尽管女方父母极力反对,认为他是个“狂野的空想家”。他购买了百亩土地,并在1771年搬到他命名为纽霍夫(Neuhof,新农场)的家。然而,由于土地贫瘠、开支超预期以及他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他的农业尝试在四年后宣告失败。
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将自己的房子变成贫困儿童之家。尽管这次慈善尝试(1775-1780年)在经济上再次失败(原因包括:收成差、不感恩的父母引诱孩子离开、仆人不诚实以及他本人缺乏财务经验),但这次经历帮助他找到了真正的使命,并奠定了他后续成就的基础。他当时的想法是:教育应结合手工劳动,从日常生活中孩子们所见的事物开始进行指导。
早期著作与教育理论
在纽霍夫期间,他对自己的儿子雅各布(Jacobli)的成长进行了细致的日记记录(1774年),这表明他试图实践卢梭的理论,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实际观察发展了自己的原则。他强调事物而非词语的重要性,并认为教育的 aim 不在于给孩子灌输知识,而在于发展他们与生俱来的才能。
1780年后,在朋友伊瑟林(Iselin)的鼓励下,裴斯泰洛齐开始写作。
- 一个隐士的晚课(The Evening Hour of a Hermit, 1780):这是他第一部教育著作,包含约八十条格言。核心观点是家庭是人类教育的基础,真正的智慧和内心的平静必须是简单、人人可及的。
- 林哈德与葛笃德(Leonard and Gertrude, 1781-1787):这部作品共四卷,是一部关于农村生活的简单而感人的故事。小说通过葛笃德(一位善良、勤劳、明智的母亲)的角色,阐述了裴斯泰洛齐关于如何教育儿童使其参与家务劳动并提升民众的观点。尽管前几卷大受欢迎,但读者多将其视为小说而非教育文本。
-
寓言(Fables, 1797)和对人类发展过程中自然进程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Course of
N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ace, 1797):这是他十年文学沉寂后出版的重要作品。尤其是《探究》,提出了他关于人从“动物人”、“社会人”发展到“道德人”的理念,强调道德人必须是自我塑造的结果。
1798年之前的学说总结:裴斯泰洛齐的工作始于对穷人的同情,最终发现教育是唯一的有效补救措施。他认为教育应从内在到外在(from within to without)发展,而不是像传统教育那样机械地从外在灌输知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调节人类发展规律的原则,即将人的教育(包括智力和道德)比作植物的生长和发展(有机发展)。
第二部分:施坦茨(1799)至纽霍夫(1825-1827)
施坦茨(Stanz, 1799)
1798年的瑞士革命为裴斯泰洛齐提供了实践机会。由于天主教州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发生大屠杀,政府决定在施坦茨建立一所孤儿院,并任命裴斯泰洛齐为院长。
他立即开始工作,接纳了大约八十名身心受创的孤儿,只依靠一名女佣协助。他的成功是惊人的和立竿见影的。他回避常规,不分班级,而是通过不断的爱和观察来对待孩子,将自己视为他们的父亲。他甚至没有教材,认为孩子与自身、与自然以及彼此之间的接触就足够了。
施坦茨的方法:他通过合唱重复的方式进行语言练习,只使用他们完全理解的词语。他重视沉默和整洁的姿势。他认为最早的教学应是简单地锻炼官能,首先是注意力、观察力和记忆力。他通过感官印象来学习数字和地理。他还采用了互助教学(mutual instruction)的概念,让大孩子教小孩子。他通过榜样(如孩子们讨论如何帮助阿尔道夫镇的受灾儿童)来教授道德和宗教,而非形式化的教条。该实验持续了六个月,因建筑被改为军医院而被迫中止。
莫尔夫(Morf)对施坦茨实验的总结强调了裴斯泰洛齐教育学的核心原则:知识必须建立在感知印象(sense-impression, Anschauung)之上;教学必须从最简单的元素开始,循序渐进,通过心理学连接的步骤,让孩子依靠自身力量达到每一个环节。
伯格多夫(Burgdorf, 1799-1804)
施坦茨实验后,裴斯泰洛齐身体虚弱但恢复了精力。他被允许在伯格多夫的一所非公民学校任教,但因教学方法非传统(例如,他忽视了《教理问答》)而再次被迫离开。他随后被任命在镇公民学校的最低年级任教(约25名5至8岁儿童)。
在伯格多夫,他继续试验和发展其方法。一次,一个孩子建议直接从真实的窗户学习,而非图画,裴斯泰洛齐接受了,这是他教学中“从自然中学习”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开始系统地简化阅读和算术的元素,进行心理学分组,并让学生在石板上画线条和角度。
1800年,一次年度考试后,学校委员会出具了高度赞扬的报告。报告指出,他展示了如何“真正地以心理学方式”培养孩子的才能,并证明了其方法远优于旧的机械方法。
他与年轻的乡村教师克鲁西(Krusi)合作,克鲁西拥有裴斯泰洛齐所缺乏的“行政能力和机智”。学校搬到了城堡,并接纳了更多的学生。该机构被描述为一个大家庭,爱和感激取代了规则和纪律。
伯格多夫的著作:
- 葛笃德如何教导她的孩子(How Gertrude Teaches her Children, 1801):被认为是裴斯泰洛齐最重要、思考最周全的教育著作。莫尔夫总结了其主要原则:感知印象是基础,教学必须遵循发展路径而非教条式阐述,教育旨在发展心智能力而非传授知识,爱是纪律的基础。
- 母亲用书(Book for Mothers, 1803):旨在为母亲们提供具体的指导,简化教学元素。这本书由克鲁西代笔,从观察孩子自身的身体开始,但由于过于冗长和详细,导致人们机械地学习,并未成功。
在政府的支持下,伯格多夫学校被改造为瑞士教师培训学院。然而,政治动荡再次袭来,政府形式改变,裴斯泰洛齐被迫寻找新的场所。
慕兴布赫塞(Munchenbuchsee, 1804-1805)与伊韦尔东(Yverdon, 1805-1825)
1804年,裴斯泰洛齐将机构迁至慕兴布赫塞的一座旧修道院。他曾短暂与农学家费伦贝格(Fellenberg)合作,但在教育和财务管理上的分歧导致合作破裂。
1805年,他将机构迁至法语区的伊韦尔东(Yverdon),在一座古城堡中安顿下来。伊韦尔东机构声名鹊起,1808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失败后,为振兴国家,派遣教师前来学习裴斯泰洛齐的方法,使该机构的国际声誉大增。
伊韦尔东的教学实践:课程基于数字、形式和语言。地理教学是革命性的,从实地考察和用粘土制作当地山谷的浮雕开始,然后才看地图。算术采用心算(mental arithmetic),使用单位表和分数表进行感知印象教学。他还引入了体操,强调渐进性。机构氛围自由,学生与老师关系友好(如一起进行军事演习和园艺)。
衰落和挑战:尽管名声在外,但机构内部问题重重。由于学生来自各国,年龄各异,“父爱”式的家庭化管理模式在大型机构中难以维持,爱心纪律逐渐瓦解。核心助教尼德雷尔(Niederer)和施密德(Schmid)之间存在尖锐的不和与争吵。裴斯泰洛齐本人在行政和财务管理上完全无能。
机构的声誉开始受到批评,批评者指出机构过于注重数学,且缺乏秩序。施密德的回归(1815年)虽然有助于管理,但加剧了内部矛盾,裴斯泰洛齐逐渐沦为施密德的工具。
1815年,裴斯泰洛齐失去了妻子安娜。
克兰迪(Clendy)婴儿学校:在伊韦尔东机构走向衰亡时,裴斯泰洛齐在附近的克兰迪(Clendy)成功地创办了一所针对贫困幼童的学校(被视为婴儿学校的起源),展现了他对教育事业永恒的爱和成功。
1825年,由于施密德被当局驱逐出境,裴斯泰洛齐带着他一起离开了伊韦尔东,机构正式关闭。
重回纽霍夫与逝世(1825-1827)
机构关闭后,裴斯泰洛齐回到了纽霍夫。他年近八十,仍坚持写作。他出版了天鹅之歌(The Swan’s Song)和我的命运(My Destiny),试图挽救其理论,并承认自己实践上的失败源于自身无能。他仍在努力实现毕生的梦想——建立一个贫困儿童之家。
他于1827年2月去世。他被安葬在比尔村(Birr)纽霍夫附近,墓碑上刻有他生前简短的墓志铭:“他为众人付出一切,却未为自己索取任何”。
裴斯泰洛齐的哲学与方法总结
本书最后章节深入探讨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哲学:
- 哲学核心:人类拥有内在的、有机发展的能力(有机发展律),真正的进步来自于内在的工作。教育者的任务是按照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协调和利用世界提供的资源。
-
道德教育:道德发展来自于情感的激发和运用,生活即教育(it is life that
educates)。 - 智力方法(Method):学习必须是主动的,来自于感知印象,而非词语。词语的价值在于固化想法,而非产生想法。教学必须循序渐进,确保孩子彻底掌握一个概念后,再进入下一个概念。
关键方法:
- 实物教学/感知印象练习(Object-lessons):教授孩子观察和描述周围的物体。
- 计算:通过单位表和分数表等视觉工具进行教学,让孩子通过感官印象理解数字关系。
- 图画练习:使用石板,训练孩子的手、眼和审美能力,作为几何和书写的准备。
- 地理教学革新:从观察实际土地和制作浮雕地图开始。
- 语言教学: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掌握母语,并尝试用此方法来学习外语。
附录(Appendix)
附录收录了裴斯泰洛齐著作的摘录和旧学生的追忆。
著作摘录:强调在施坦茨的工作中,教育力量来自于孩子们和谐的共同生活、共同的注意力和需求,而非外部约束或说教。他相信要先唤醒孩子们纯粹的道德情感,并让其通过日常经验形成对是非的判断。他还批评当时的流行教育是“词语和外表的教育”,如梦般空洞,并重申感知印象是知识的真正基础。在《天鹅之歌》的序言中,他请求读者认真审视其作品,以发现那些可能造福人类的真理。
学生回忆:学生们回忆裴斯泰洛齐外表不拘小节(如裤子和袜子松垮),但目光敏锐、充满慈爱。他依靠爱心纪律控制学生。有学生指出,尽管裴斯泰洛齐在短时间内似乎没有教授“实证知识”,但其方法在于“准备花瓶而非装满花瓶”,为孩子们后来的快速进步奠定了基础。地理学家查尔斯·里特(Charles Ritter)称赞裴斯泰洛齐拥有伟大的心胸和天赋,尽管他自己无法应用最简单的教学细节,但他能将理念传达给助教。
总结与评论
该书详尽地描绘了裴斯泰洛齐充满矛盾、英雄主义和屡败屡战的一生。他的生活(尤其是前期的纽霍夫时期)本身就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这本书成功地突出了裴斯泰洛齐对现代教育的根本性贡献:他将教育学建立在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和感知印象之上,并强调了教育必须结合心、脑、体有机和谐发展(organic development)。他的失败(无论是农业、慈善机构还是伊韦尔东的行政管理)通常源于他的不切实际、管理无能和过度信任,但他的核心教育理念因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穷人的无限爱心而永垂不朽。
形象比喻: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就像一位农夫对待幼苗。他不是简单地将外来的果实(知识)捆绑到幼苗(孩子)身上,而是通过提供适当的环境和养分(感知印象和实践),耐心地等待和引导幼苗内在的生命力(天赋和能力)自然地生长、发芽、开花和结果。他帮助孩子们从内部进行自我塑造,成为独立的“道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