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202
《存在主义后记及其他随笔》
Postscript
on Existenti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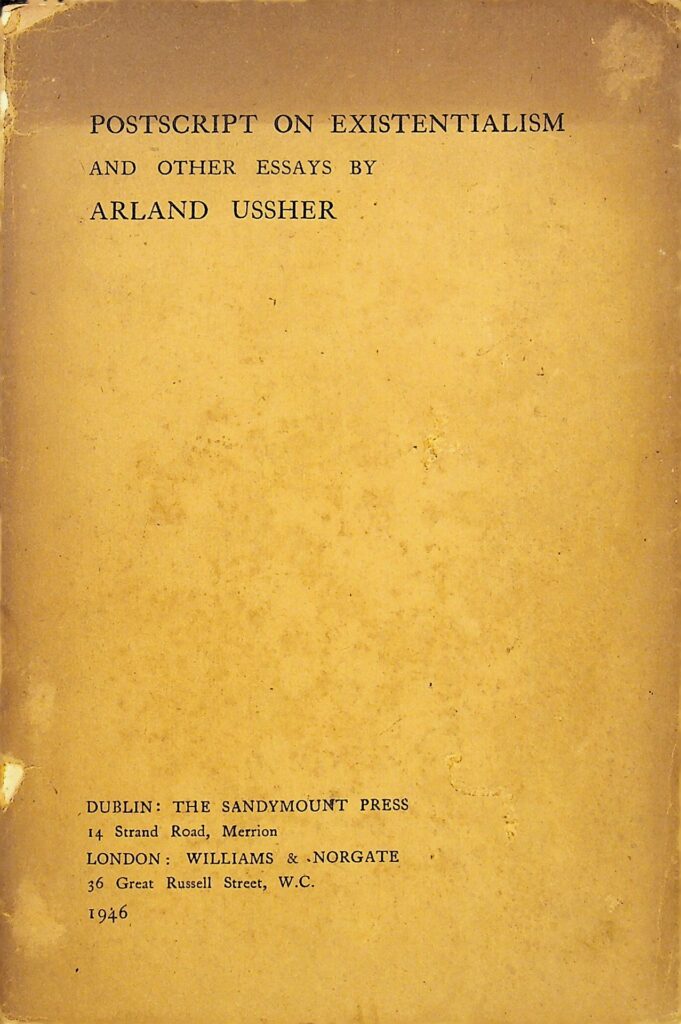
《存在主义后记及其他随笔》,作者是阿兰·厄舍(Arland Ussher),于 1946 年出版,涵盖了他写于 1937 年至 1945 年间的散文。这些文章代表了作者对欧洲思想的思考历程,尤其是在纳粹主义兴衰的十年间。厄舍在书中探讨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和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哲学背景和政治走向,通过对文化、政治、宗教和哲学概念(如存在主义、凯撒主义、悲剧的终结、原子弹的影响)的比较分析,深入考察了欧洲的内在冲突和文明的命运。他试图关联生活、文学与哲学,文章充满发人深省且有时颇具争议的观点,挑战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观念。
这部由阿兰德·厄舍(Arland Ussher)撰写的《存在主义后记及其他随笔》(POSTSCRIPT ON EXISTENTIALISM and Other Essays),于 1946 年出版,是作者在纳粹主义兴衰的十年间,“穿行欧洲思想”的记录。厄舍先生长期在欧洲大陆进行研究,从个人视角剖析欧洲人的心理构成,从而生动地揭示了各国深刻的背景和当前的趋势。
I. 《最好的与好的》(The Best and the Good)(1937年)
本章探讨了“最好的是好的敌人”这一观点。作者阐述说,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典范往往与其规范(norm)相悖。例如,最大的创新者基督出自最传统主义的犹太民族;精致的英格兰的幻想和抒情主义与该民族典型的实际和物质成功形成钻石与煤炭的关系;法国的“享乐主义者”是该国军事和传教士圣徒的对立面。同样,普通的德国人的温和与柔顺正是催生“超人”(demoniac force)所需的特质。作者还提及“难以理喻的爱尔兰人”,他们拒不屈服,其玩世不恭和背叛性的客观性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民族或帝国,但偶尔也能开出最纯洁的个人奉献之花。本章将基督视为犹太人的原型(antitype),指出在他出现之前,世界上只有命运,而没有真正的悲剧。
II. 《甜蜜的敌人》(The Sweet Enemy)(1938年)
本章比较了欧洲三大主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像“教师”,德国人像一个总是从固定前提出发的“听话男孩”,而法国人则固执地保持着“迷人的可塑性”(charming
plasticity of youth)。尽管法国拥有智慧,但其进步缓慢,这种滞后是不可否认且可能是致命的。作者认为,法国人满足于做一个“糟糕的天主教徒”,这比英国人做异教徒或德国人做怪物利己主义者要好。法国半讽刺性的传统主义阻止了他们内部冲突的片面解决,但也阻碍了“神圣的和谐”。法国被视为一面镜子,欧洲在接下来的各个阶段都通过它来审视自己。法国人对限制的接受解释了法国的虚荣(为观者而存在的镜子)、资产阶级骄傲(保持镜子完整)和革命暴力(镜子破碎时彻底破裂)。然而,由于法国“相对不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其重要性注定会下降,可能沦为一个“不景气的地区”。法国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但不能产生先知,其“受难”也不会带来救赎。
III. 《未竟的命运》(The
Destiny Manqué)(1938年)
本章将男性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天才”,女性的最高境界为“辨识男性的天才的能力”。作者认为,英国(本质上是男性民族)的危险在于用“性格”(Character,天才的二流普及版)代替了天才。而德国(本质上是女性民族)的危险在于用“意识形态”(Ideology,直觉的低级普及版)代替了直觉。英国人对“性格”的迷恋在政治上是有益的。而德国人对“理想”的无限服从则在政治领域成了祸害,将其女性化的虔诚贬低为女巫的狂热。德国的悲剧在于其像一位英勇奉献的女性,却浪费在无能或卑劣的人身上。由于对忠诚永不满足的需求,德国人在政治上给人一种不忠的印象。作者指出,现代民族主义在德国达到了荒谬的极致,因为德国的灵魂必须从外部受精。国际性的高卢文明曾在俾斯麦时代前对德国产生积极影响,而后来出现的犹太人(这个模棱两可的东方人)被视为过于犬儒和疏远,未能在德国扮演“白马王子”的角色。德国因错失了伟大的命运,像中世纪的“老处女”一样,狂热地转向魔鬼崇拜。
IV. 《永恒的村民》(The Eternal Villager)(1938年)
本章旨在评估英国独特的民族类型。作者承认,欧洲大陆民族大体上受“真理”(Veritas)观念的统治,而英国人则受更理性、更现实的“诚实”(Honesty)观念的统治。欧洲的秩序是人为了国家,国家为了上帝;而岛国民族则颠倒了这一点:上帝为了英格兰,英格兰为了英国人,英国人为了英国的女人和孩子。英国人是与时间相符的,因为时间的顺序是从抽象到局部,从理性到现实。然而,英国人的力量是某种巨大的原始推力的“惯性”,他们的类型已经凝固到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程度。英国的精神在自由中前进,但不能真正徘徊,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像阿尔比恩的悬崖一样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真实的英格兰永远是“乡村”(village),在那里,公众舆论比任何法律都强大、微妙和普遍。英国场景中的多样化角色掩盖了英国灵魂的“完全同质性”。莎士比亚、雪莱等作家被誉为“创造者”而非“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的氛围是玩具剧场的不真实感,缺乏真正的张力或冲突。英国人会在孩子(如珀尔迪塔、露西·格雷)或充满“感情谬误”(pathetic fallacy)的风景中寻找美。不列颠尼亚是赫拉斯(诗意的希腊)与罗马(务实的罗马)的结合体,生下了彼得潘。英国是一只“正在孵蛋的母鸡,但她的那颗蛋很久以前就冷了”。
V. 《日食》(Eclipse)(1938年)
作者指出 1914-1918 年大战的多个解释(德国侵略、德国惧怕俄国、俄国惧怕革命)都是正确的。现在,由于大多数人将“时间”或向无形式的向心吸引力奉为神祇,问题再次明确。德国帝国主义的负面拉力受到俄国共产主义更巨大的负面拉力的制约,而后者又受到对未来和非理性的恐惧的制约。作者预言,下一场“大战”将是欧洲历史形式的“最后一搏”;即使表面上获胜,守卫者也会在实质上失去一切,与无政府状态的代表无异。作者认为,在内部张力较小的地区,个人或小型社会可能会幸存下来并获得极化刚性。
VI. 《第三王国》(The Third Kingdom)(1939年)
本章对比了静态/古典的世界观(法国人,思考财产和安全)和动态/现代的世界观(德国人,思考效率和“危险地生活”)。法国语言适合“优雅而排外的奥林匹斯神”,而德国语句(像波浪一样冲向动词)象征着“粗鲁、急切的泰坦族”。在众神的黄昏时代(黑格尔的力量世界取代了柏拉图的形式世界),法国注定会逐步失去重要性。原子化的人格或民族主义(民主)正在从内部和外部瓦解。德国军国主义(锤子)最终将会在使用它的“巨人混沌”(俄罗斯平原的散发物)手中破碎。条顿人是帝国的“冲击者”,而不是“建造者”。德国对无限的渴望最终导向了俄罗斯的虚无主义。
作者提出存在第三种神性:机智(Tact)——它是介于传统和变化之间的调解者。机智是所有力量的平衡形式,它融合了原始能量和原始物质,创造了世界。它可能会在混乱中创造出一种比过去文明更个性化、更不抽象的世界秩序。
VII. 《创造与虚无主义》(Creation
and Nihilism)(1939年)
人类关注于弥合距离,象征着现代人面临的“内心虚无”——基督教在自我与灵魂之间引入的精神裂隙。现代人需要“艺术般的天赋”所具备的完美“机智”来抛绳过隙,这一阶段充满危险。缺乏目标的长远眼光导致了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恶魔般的展示。作者指出,尽管纳粹主义的“毒龙”令人恐惧,但创造性的天才“在现实中属于魔鬼的派对”。西方国家应对德国的自卫措施,以及对自身而言的自我表达方式,都要求权力下放(decentralisation)。德国富有成效的发酵力被压缩在“民族”的固定概念内,变得贫瘠而具有爆炸性。邪恶的行为通常是艺术本能被阻塞的表现。通过内在分裂和去中心化,可以允许单位之间进行创造性的竞争。作者建议以法国的现实主义将此机制强加于敌国,以英国的进步性将此机制应用于自身。
VIII. 《两种挑战》(The Two
Challenges)(1939年)
德国人的优点是古老的“尊敬”(Homage)本能,但其缺点是缺乏“品味”(Taste),使其必然爱上最粗俗的事物。德国人不断地被“不完整性”折磨,因此无法创造一个真正的民族或产生一个值得尊敬的首领。德国的领袖们(从路德到希特勒)都是怪异但充满活力的。1914 年的德国挑战(普鲁士贵族式)是解放的智力与意志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抗。它瓦解了商业庸俗主义,使人们更接近物理和形而上学的现实。但新德国(流行化、虚假神秘、残暴感伤)像一个战败的剑客,质疑裁判并要求重新决斗。这种针对风度和品味的精神所犯下的罪恶,使其难以被宽恕。
IX. 《巴黎沦陷》(On the Fall of Paris)
作者指出,巴黎的沦陷引起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恐惧和怜悯。法国是一个希腊式的“主角”,陷入了无用而沉默的痛苦。法国的缺点是“早期、更具人性化的文明”的缺点(如效率低下、公共腐败、地方主义)。法国的政治权力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是完全达尔文主义的动物,其技能在于不断、无限敏感的适应。她的灵魂的弱点在于永久的孤立,而她的力量在于无法被摧毁。
X. 《中立的民族》(The Neutral Nation)(1941年)
本章将英国和爱尔兰比作被锁在一起的兄弟:英国人向外看变化的土地,爱尔兰人只看海面。罗马文明、中世纪主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自由主义等欧洲进程几乎没有触及爱尔兰。爱尔兰沉浸在“经院哲学式的沉睡”中,以至于将极权主义爆发仅视为“帝国主义的冲突”。作者指出,爱尔兰有理由回答“没有说过 A 的人不必说 Z”。爱尔兰是唯一一个坚持普遍概念和先验推理的高度文明国家,其经院哲学训练产生了乔伊斯式的“辉煌的迂腐”和德瓦莱拉式的“沉闷的迂腐”。爱尔兰的超然理性主义可能为英国不安分的实用主义提供新社会综合的元素(正如哲学家在伯克利身上找到了形而上学家,艺术家在王尔德身上找到了美学家的先例)。
XI. 《德国人和他的影子》(The German and his
Doppelgaenger)(1941年)
作者认为理解德国当前的疯狂必须考察其对犹太人“病态般的仇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深刻的精神血缘关系。两者都缺乏对物理和心理距离的敬畏,都是侵略者、搅动者。两者都擅长抽象和分解性的艺术与科学(音乐和物理学)。两者轮流表现为神秘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他们在实践中具有互补性:德国人是可塑、强大、愚蠢的;犹太人是几乎不可同化、弱小但智慧的。作者认为,站在现代时代背后的希伯来先知(马克思)是最负面的人物,他宣扬为未来种族而牺牲。德国对“终点”日益明显的空虚感到幻灭,转而将“手段”本身理想化,把战争和革命国家视为目的。德国作恶是为了摧毁客观的善恶概念——即犹太人创造的善恶概念。
XII. 《罪恶之谜》(The
Mystery of Iniquity)(1942年)
文明国家对 1939 年灾难的毫无准备,具有“催眠”的特质,即故意拒绝相信“诚实的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可悲的卓别林式元首会犯下众所周知的行为。这接近于邪恶的中心奥秘和民主的特殊危险。人民(The ‘People’)既是上帝也是野兽,是善恶的无限放大。作者追溯了基督教思想的线索:从基督的“爱让我们在上帝中合一”,到中世纪的“合一在于善”,到文艺复兴的“合一在于理性”,到浪漫主义的“合一在于感觉”,到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合一在于组织/机器”,最终到生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合一在于我(群众人)”——即“我就是上帝”。思想的线索已经解开,“善”的理念已经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达到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不是抽象,而是创造;不是“道”,而是“行动”。这个新时代将致力于“美”的理念,但作者提醒:美接近于煽情主义和残忍,而善几乎与真理对立。
XIII. 《凯撒主义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of Caesarism)(1943年)
当前世界的危机是上帝与凯撒的对立。自 16 世纪以来解放的个人/民族自我意志,现在已经脱离了先验宗教和理性/人道主义的假设。世界正日益成为新凯撒主义(mass-leader and
crowned demagogue)的领地,它是上帝的直接对立面。凯撒主义的哲学来自于凯撒的故土意大利。意大利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詹蒂莱)为文明的终结阶段发展了“行动主义”或“未来主义”,满足于充当凯撒审视自身的眼睛。“政治的艺术”是一种“巴洛克式”的私生艺术,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政治束缚了行动,而艺术解放了精神。意大利人将权力形而上学作为缓解自身无能的补药,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将其“辩证法”视为一种将艺术和宗教作为平行杠的精神体操,将一与多融合到凯撒帝国的原始黑暗洪流中。詹蒂莱的“实在唯心主义”是自由主义进步论的抽象延伸,应用于 20 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技术。作者总结说,意大利的形而上学思想接近于真理(如哲学是存在而非知识,现实是具体的、个人的,支配不是自由,世界没有目的),但她错失了救赎之路。
XIV. 《悲剧的终结》(The End
of Tragedy)(1944年)
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后期小册子(如《西方的没落》)有助于理解德国为何走上歧途。斯宾格勒与希特勒有着奇怪的平行人生。他们都厌恶和平宁静的世界,感谢大战的到来,渴望魏玛共和国的结束,蔑视那些宁愿选择幸福而非民族“伟大”的普通人。斯宾格勒不断重复,人类最优秀时是“野兽”(Raubtier)。他认为西方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是悲剧性的,追求冲突、挑战命运。但在文明的“理性主义”死亡阶段,勇敢的灵魂只能通过玩“权力政治和世界大战的游戏”来注入生命之酒。斯科特在南极的牺牲(1912年)是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天真的、自愿的行动。此后,“勇敢的旧世界”结束,悲剧变成了恶魔性。在文明的西方诞生了讽刺精神(Ironic
spirit)——一种内在的、内敛的完整性,它厌恶艺术上的过度强调和不人道的机械性。这是喜剧性(Comic,如但丁的《神曲》),是悲剧的嘲弄面。西方灵魂的复杂性解放了人们,不再受制于血统,也不再受制于“时间之神”。和平不必是可耻的,因为人们学到了一种比宿命论的行动辩证法更坚硬、更愉快的“情绪辩证法”。浮士德式的人已经死亡,但被拯救了。
XV. 《德国人与英国人》(Germans and English)(1944年)
英国人和德国人这两个充满活力和帝国主义思想的种族,在一个方面互补:英国人是“生命的天才”,德国人是“死亡的天才”。他们分别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辩证主义者,客观/主观,乐观/悲剧,诗意/音乐性。作者以叔本华的哲学为例(将生命视为只在自我放弃时才自由的“意志”)。这种“阴郁而尖刻的形而上学空气”使普通德国人变得僵硬、麻木,成为任何“思想”蛊惑者的奴隶。只有当他将世界置于脚下,才能找到和平。作者认为,对德国人的改造不应是强加给他们陌生的实证主义,而应该是将他们过于抽象的心灵召回到不那么宏大、更亲密、非政治化和静默的“路德式信仰”。
XVI. 《盎格鲁人还是天使?》(Angli
or Angeli?)(1945年)
英国人蔑视逻辑,声称理性行动带来了物质成功和道德卓越。尽管如此,作者指出其“铁石心肠的讽刺性的自我反省”仍然存在。凯泽林认为英国人是“动物性的”(animal-like),由本能或更高的直觉指导。英国人可能是真正的人类(Homo
Sapiens),是万能的平衡者。而欧洲大陆人则像固定的动物物种。英国人只改变了其“偶然性”,而没有改变其“本质”——即其类型必须生存的意志。英国人是“直面生命的动物”(life-confronting
animal),像奥德修斯一样调整风帆以适应环境。他是一个博物学家(naturalist),但很少是唯物主义者;有宗教信仰,但从未真正形而上学。他将任何对“变动”(flux)的把握视为“病态”的死亡欲望。对于英国人来说,道德是为生命服务的,而不是生命为道德服务。这使他比仰望“理智之美”的天使稍逊一筹。人类的幸福在于思考,将“生命”的丛林转化为精神的花园。
XVII. 《奇异的命运》(The
Strange Destiny)(1945年)
以色列的历史命运与最伟大的犹太人(耶稣)密不可分。犹太民族是西方人负罪感的“非自愿牺牲品”。对犹太人的仇恨部分是对基督的仇恨,也是对自身良心的恐惧和愤怒。作者指出,耶稣是以色列的缩影和镜子,但也是一种“反转”(inversion)。耶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而普通犹太人“非常明确地属于这个世界”。犹太人是渴望在世间安居乐业的民族,他们拥有乐观的宗教,期待着地上的乐园。非以色列人渴望“解放”和消融。正是来自一个相信成功、鄙视廉价悲情(如战争、浪漫、超世俗希望)的现实而充满活力的民族,才能发出十字架上“裂开内在存在”的呼喊。
XVIII. 《斯拉夫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lav)(1945年)
俄罗斯人存在着矛盾:行为上疯狂而残忍,但他们的文学给人类灵魂带来了最甜蜜的滋养。作者提到俄罗斯的魅力在于其人性,但这个“永恒的孩子和野蛮人”可能成为最大的威胁。俄罗斯人接受暴政和不公是自然的,但谴责邪恶。他们的本能屈服于内心所谴责的事物,导致其性格中致命的“二分法”。俄罗斯人是早期的/东方基督徒,可能在真实的悲剧意义上成为“人类的敌人”。德国向俄罗斯屈服,是因为它遭遇了将幻想变为彻底现实的“实体平等”。对于西方基督教传统而言,任何新的救世主主义都是邪恶的(现代神权国家的恐怖)。如果共产主义降临西方,那将不是“启蒙”,而是纯粹的厌倦和内向的恶意。俄罗斯文学中耸立着基督和宗教大法官两个巨大形象,宗教大法官同样是人性的“爱人者”。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决心让西方价值观生存下去,就必须发现基督在彼拉多面前未曾说出的答案。
XIX. 《原子弹的预兆》(The
Augury of the Atom-Bomb)(1945年)
作者宣称,“希望夫人”(Lady Hope)于 1945 年 8 月 6 日彻底死亡。原子弹爆炸象征着原子自我或个体性的崩解。人类一直深信的“不朽”(家族延续)现在也变得充满疑问。所有关于“物质”的言论都是矛盾的。“驾驭自然的力量”必然导致腐败。希特勒的幽灵仍在欧洲徘徊。人类无法被理性化;“像神的人”将永远是魔鬼。犹太人(“道”的承载者、先知、科学家)的领导结束了。德国(试图摧毁犹太人的最年轻的民族)感受到了最古老民族的精神枷锁。德国以火(如耶和华以水)淹没了世界。避难所只存在于不确定性的地方。
XX. 《存在主义的附言》(Postscript on
Existentialism)(1946年)
退却的条顿浪潮在法国留下了“存在主义”的萌芽,它吸引了只要求“赤裸存在”的人类的注意。存在主义可以比作一个“新学生”在一个陌生领域中,战栗地意识到自己独特实体的复杂感受。萨特(Sartre)的观点“正是通过我为‘他者’的客观性的揭示,我才领会到他的主体性的存在”,颠倒了传统的唯心主义观念。存在主义者从笛卡尔的终点开始:“我受苦,因此有不属于我的东西造成了我的不适。我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我是一个处境(situation)”。对“邪恶”的重新发现(人生的引力原理)为哲学带来了张力。
作者认为,唯心主义(黑格尔)对“非我”的回答是错误的,将世界简化为机器零件。一切皆有可能,因此一切皆不真实。这导致了唯心主义的双重产物:生命主义(部分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法国人则试图在“浪漫的讽刺”下掩盖深渊。最终逻辑结论是“无谓之罪”(crime gratuit)。
萨特转向了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学说。克尔凯郭尔强调有限的生物注定不幸福,因为它受制于非理性,必须通过“同样荒谬的自我选择”重新融入神圣理性。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D. H. 劳伦斯可能是先驱。劳伦斯也将生命视为通过“放弃意志”来实现“自我创造”。作者警告,拉丁人(如法国人)即使在非理性中也保持理性主义,他们认为命名一个理念就是理解它。因此,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可能必须放弃逻辑的“旅行指南”。萨特的存在主义带有政治色彩(抵抗运动的“投入行动”,s’engager),而政治是法国和欧洲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