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元章藏书0149
《耶稣基督与世界宗教》
Jesus
Christ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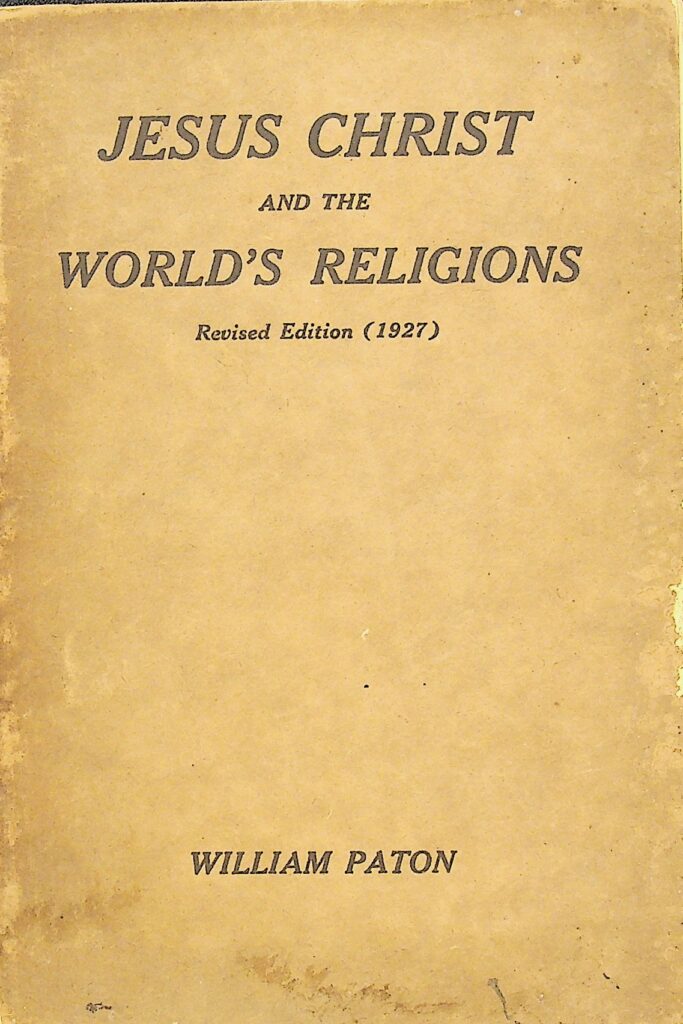
《耶稣基督与世界宗教》的书的节选,概述了世界主要非基督教宗教的特征和历史。文本首先介绍了原始宗教,强调其以恐惧为主导的万物有灵论;接着详细探讨了伊斯兰教的起源、核心教义(如对独一真神安拉的信仰)、《古兰经》的作用,以及其社会缺陷;随后是关于印度教的描述,涵盖了《吠陀经》、种姓制度、业力(Karma)和解脱(Moksha)等核心理念。文本还讨论了佛教,从佛陀的生平开始,解释了四圣谛和涅槃的概念。最后,概述了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教和本土佛教宗派。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基督教如何以其关于上帝、救赎和人性的启示,来回应和满足这些非基督教信仰所揭示的人类精神需求。
《耶稣基督与世界宗教》(Jesus Christ and the World’s Religions)一书由威廉·佩顿(William Paton, M.A.)撰写,第一版于 1916 年 11 月出版,修订版(第二版)于 1927 年 9 月出版。
本书旨在为那些希望简要了解非基督教宗教主要特征的读者提供一份简明扼要的陈述。尽管篇幅较短,但作者力求呈现一幅大致可靠的图景。作者强调,深入研究这些宗教能够加深对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的至高无上的信念和欣赏。
总览
该书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威望下降、基督教文明受到广泛挑战的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向世界阐释基督教信息。作者威廉·佩顿在书中详细探讨了基督教针对全球主要宗教体系和原始信仰应传达的核心信息。
第一章:基督教给原始民族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Primitive
Peoples)
本章开篇指出,人类无论文化高低,都普遍具有宗教性。这种宗教观点的普遍存在并非对信仰的威胁,反而为最高和最真实的启示最终能被所有人理解提供了希望。
宗教的定义包含三个要素:相信存在更高的力量、敬拜它们的意愿以及对它们的依赖感。原始宗教的总体特点可以概括为“崇拜精灵”(Animism)。这些精灵包括死去的祖先、自然界(山、海、森林)中的精灵,以及神物(fetishes)。这种信念主要源于对梦境的解释,即将灵魂视为身体的影像,可以随意离开身体。
原始宗教的实践中,恐惧是主要的驱动力。人们必须通过崇拜和献祭来避免精灵的恶意。这种宗教观几乎完全缺乏宗教慰藉,祈祷和献祭所求的都是物质利益。同时,它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善恶”概念,只有部落习俗,而精灵通常被视为邪恶或非道德的。社会层面,原始宗教与部落生活紧密交织,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虽然迷信有时能保障法律和财产(例如防止弱者被欺负),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例如一夫多妻制带来的羞辱,以及对妇女和双胞胎的恶劣对待。
基督教的信息: 基督教带来了一位慈爱且全能的上帝的信息。对于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来说,上帝是友善且大能的这一观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原始宗教信徒而言,救赎主要意味着从邪灵的力量中被解救出来。当他们相信基督比恶魔更强大时,邪灵便不再拥有辖制他们的能力。随着他们对上帝品格的理解加深,才会开始明白罪的含义以及基督不仅能救他们脱离恶魔,还能救他们脱离罪。此外,基督徒对永生的希望也强烈地吸引着那些只有模糊和苍白来世概念的原始民族。
第二章:基督教给穆斯林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Moslems)
伊斯兰教是所有主要非基督教宗教中出现最晚的,它明确地拒绝基督教,并将穆罕默德置于基督之上,视为上帝给世界的“最终话语”。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早期的阿拉伯宗教是部落多神论,混合了原始的精灵崇拜(如“精灵/Jinns”)。“安拉”(Allah,意为“神性”)的概念在穆罕默德出现时开始凸显。穆罕默德(生于约 A.D. 570 年)
在麦加(Mecca)传教受迫害,后逃往麦地那(Medina)(“希吉拉/Hegira”),这一事件成为穆斯林计史的起点。在麦地那,穆罕默德成为了社群的领袖和立法者,并采用了古老的偶像崇拜仪式(如亲吻黑石、环绕克尔白/Kaaba)。
伊斯兰教义的核心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穆斯林对上帝的独一性和主权怀有强烈的信念。然而,安拉的品格与耶稣基督的父神有巨大差异:安拉很难被称为**“神圣”**(Holy),其道德品格被认为是变化无常的。其次,安拉与人类完全分离,父子关系的概念对穆斯林来说是亵渎。
**穆罕默德和《古兰经》**被视为最终和绝对的标准。穆罕默德的人格和生活为穆斯林社会设定了标准。《古兰经》被认为是上帝直接、口头无误且永恒的言语,但其内容也夹杂着道德弱点和个人偏见(例如对天堂的感官享受描述)。
伊斯兰教的缺陷体现在对女性的低劣看法(认为女性主要只是性的存在)和一夫多妻制上。由于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是绝对权威,这限制了社会的进步。尽管后来出现了发展变化,例如穆罕默德和《古兰经》被神化、神秘主义(苏菲派,德尔维希/Dervishes)的发展,以及什叶派(Shi’ite)对赎罪(阿訇哈桑和侯赛因的牺牲)的强调,但这些都反映出穆斯林的上帝观并不能满足人心的渴望。
基督教的信息: 由于穆斯林对基督教的偏见和不了解,基督教的首要信息必须是爱与服务(例如传教学校和医院)。耶稣基督的品格对穆斯林极具吸引力。他们需要通过基督来认识上帝的伦理品格(父爱)。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上帝是爱,并与人类在圣子中分享神圣生命)对于撼动伊斯兰教的静止文明和律法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否定这一真理会切断人与上帝的生命联系。
第三章:基督教给印度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India)
印度是一个认真对待精神事务的国度。本章主要关注印度教,它没有单一的创始人,是一种融合了简单偶像崇拜、高深哲学思想和真正圣洁的宗教。
早期经典(吠陀/Vedas): 约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定居者的宗教,是“快乐和愉悦的宗教”,崇拜自然神(如伐楼那/Varuna,因陀罗/Indra)。其中一些赞美诗接近一神论,但总体趋势是走向泛神论(Pantheism),认为所有神都是一体的。 后期经典(婆罗门书/Brahmanas 和奥义书/Upanishads): 强调祭司阶层和复杂的仪式。上帝被视为**“梵”(Brahma,中性)**,即宇宙的本质、全部的实在,非人格化,无法定义。人魂(atma)被认为与至高无上的自我(Paramatma)同一。
种姓制度(Caste): 婆罗门(祭司)是最高种姓。种姓制度是宗教禁忌、肤色情感和社会功能结合的产物,极其森严,是印度进步的最大枷锁。贱民(Outcastes)被完全排除在外,触摸或靠近都可能污染种姓人。
三大教义:
- 轮回(Samsara/Wandering): 灵魂在许多生命阶段和身体(人或动物)中徘徊。
- 业力(Karma/Works): 所有行为都产生不可避免的果实,严格决定下一生的境况。业力缺乏救赎或宽恕的理念。它剥夺了服务的本质意义,因为所有美德,包括自我牺牲,都必须是自我关照的。
- 解脱(Moksha/Release): 逃离轮回和业力之链。通过吸收融入至高本体(梵)而获得,这只能通过神圣的启示获得,而非善功。
阿凡达(Avatar/化身)的出现: 公元 500 年左右,为应对佛教的“冷淡道德”和满足宗教需求,印度教发展出化身的概念。毗湿奴(Vishnu,保护神)和湿婆(Siva,毁灭神)是主要的化身。特别是《薄伽梵歌》(Bhagavad-gita)将克里希纳(Krishna)描绘为至高者的化身,教导出于对上帝的爱而履行职责。然而,化身概念的危险在于,围绕英雄聚集的传说良莠不齐,导致道德价值差异巨大的神灵被纳入神谱。
后期哲学与运动: 9 世纪,商羯罗(Sankaracharya)的**吠檀多哲学(Vedanta)**将宇宙视为幻觉(Maya),解脱在于打破幻觉,认识到自我与梵的同一性。公元 1400-1800 年间,**虔诚派(Bhakti)**兴起,强调一位可以被崇拜的“人格化上帝”和个人的虔诚。
贱民的宗教与上述发展无关,本质上仍是原始的精灵崇拜(Animism),其社会和宗教状况都极为堕落,正统印度教对他们无所帮助。
基督教的信息:
- 带来上帝的信息: 印度教的两种倾向(抽象的非人格世界精神 vs. 有限的个人化身)在基督的启示中得到满足。基督启示的上帝既是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又通过人类历史明确地展示了祂的爱。
- 带来宽恕: 印度渴望救赎,但通常是从世界的痛苦和幻觉中解脱,而非从罪的权势和罪疚中解脱。基督教带来了一位圣洁的上帝,祂的宽恕不是对邪恶的纵容,而是在上帝心中承担罪孽。
- 基督的品格: 耶稣基督的品格、自我否定、谦逊和爱深深吸引着印度教徒。
- 带来弟兄情谊(Brotherhood): 基督教与种姓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种姓制度在内部建立有限的兄弟情谊,但绝对否定所有其他人。这使得贱民大量涌入基督教会。
- 带来实践的宗教: 基督教将生命视为上帝旨意得以实现的地方。信仰基督能将印度从对现世的悲观桎梏中解放出来,带来一种真正的、实践性的圣洁和救恩。
第四章:基督教给佛教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Buddhism)
佛教在全球拥有大量信徒,但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且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大乘/Mahayana和小乘/Hinayana)。本章主要关注更接近原始类型的南传佛教。
创始人(释迦牟尼/Gautama): 生于公元前 6 世纪末或 5 世纪初。放弃王子的生活,投身苦行,寻求解决人类痛苦的方法。他在菩提树下开悟:痛苦源于“渴望”(Desire),通过内在修养和对他人的爱可以脱离这种渴望,从而摆脱个人存在的诅咒。他用 45 年传道,建立了僧团(Sangha)。他引导门徒关注他所传的“真理”而非他个人。
四圣谛(Four Truths): 1. 痛苦(Suffering)。2. 痛苦的原因是“渴望”(对生命的贪恋)。3. 痛苦的止息(渴望的熄灭)。4. 止息痛苦的方法:八正道(Noble Eightfold Way)。 业力(Karma): 佛陀否认“灵魂”或“自我”的独立存在。他认为,“渴望”与前世行为(业力)的总和创造了一个新的“存在”。摆脱这种不断产生新存在的痛苦的唯一途径是消除渴望。 涅槃(Nirvana): 佛陀教义中没有上帝或灵魂的概念,因此涅槃并非“融入神性”。涅槃是八正道第四阶段所达到的彻底平静、圣洁、没有渴望的状态,可以在今生达到。由于渴望消失,业力被打破,身体死亡后将不再形成新的“灵魂”,因此很难与“非存在”区分开。
僧团(The Order/Sangha): 僧侣发誓守贞和守贫。他们遵循“三归依”(皈依佛、法/教义、僧/僧团)和十戒。僧团是佛教传播的关键。
后期佛教的发展: 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 250 年)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发展。北传佛教(Mahayana)偏离了原始教义,将佛陀神化,发展出菩萨(Bodhisatwas,如慈悲女神观音/Kuan-Yin),用物质的天堂取代了涅槃,甚至在藏传佛教中发展出了转经轮(Prayer
by machinery)。
基督教的信息:
- 带来父神启示: 佛陀对上帝保持沉默,而基督教填补了这一空白。佛教的历史表明,宗教若持续否定上帝是徒劳的。
- 带来对人的正确看法: 基督将人性中的渴望视为需要被净化和管教的,并将身体视为圣灵的殿,这与佛陀消极地看待生命和身体,试图逐渐清除生命的做法形成对比。
- 带来从罪中拯救的信息: 佛教的业力观虽然能起到道德激励作用,但其美德往往是自私的“功德”。佛教对于那些在挣扎中跌倒的灵魂没有帮助。基督教以爱为律法,通过上帝的饶恕之爱(这爱不纵容罪,而是在自身中承担罪),使人产生对罪的真实意识和对恢复与上帝团契的需要。
第五章:基督教给中国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China)
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是务实、朴实,并以其社会和民族历史为荣。中国宗教是一个复杂体系,通常一个人同时信仰儒家、佛家和道家三种宗教。
孔子(Confucius): (生于公元前 551 年)是“典型的中国人”,他的生活和著述固化了典型的中国生活观和宗教观。他整理了经典,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和政治家。 孔子前的宗教:
- 上帝(Shang-Ti)崇拜: 一种真正高尚的精神理念,由皇帝作为人民的最高祭司进行正式崇拜。通常被称为“天”(Tien)。这种至高无上的神远离个人敬拜。
- 祖先崇拜: 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宗教”。它强调家族和宗族的纽带,对逝者敬拜(牌位)。
- 精灵崇拜: 存在大量神祇和民间传说。
儒家思想: 核心是**“互惠”(reciprocity)**,强调五常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孝道是中国最强大的道德力量。儒家思想主要关注国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对上帝和来世保持沉默,认为“未知生,焉知死”(agnosticism)。 儒家伦理: 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忠诚和真诚”),给出了消极形式的“黄金法则”。但其道德有局限性,例如不能理解“以德报怨”,并且缺乏对人罪恶本质的理解,倾向于将错误归咎于无知。 经典的重要性: 五经和四书是儒家的圣书。它们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核心。
道教(Taoism): 创始人老子(Lao-tzu,约公元前 604 年),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核心概念是**“道”**(Tao/Way/Principle),即自然界背后的原则。理想是“无为”(wu wei),顺应自然。然而,今天的道教与老子的哲学关系不大,成为了迷信、风水、算命和法术的大杂烩。
中国佛教: 在中国,涅槃的概念在实践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物质的天堂。佛教通过菩萨(如观音)的自我牺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保持了**“救赎”**的观念。许多对救赎概念理解迅速的皈依者都曾是佛教徒。
现代变化: 现代革命正在冲击中国古老的障碍。废除古代经典教育代之以西方科学和文化,正在产生深远影响。
基督教的信息:
- 独一的父神: 基督教带来了在耶稣基督里启示的独一的父神的信息,以应对旧信仰的迷信。
- 崇高的道德标准与救赎: 基督教的道德标准高于孔子,更富柔情,也更实用。它不仅提供忠告,更提供救赎的力量。
- 永生与希望: 中国从未有过清晰的永生希望。基督教的希望是清晰而明确的。
第六章:基督教给日本的信息 (The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to Japan)
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物质文明发展迅速,但道德和精神标准并未相应提升。
日本的宗教: 神道教(Shintoism,本土宗教)、儒教(影响下降)和佛教(大乘体系)。 神道教: 起源于古代的精灵崇拜(Animism)和自然崇拜(如太阳女神天照/Amaterasu)。其核心要素是部落和民族的敬畏(Mikado
Cult),天皇(Mikado)是太阳神和天神的地上代表。这导致了强烈的宗教爱国主义。 神道伦理: 道德水平不高,主要关注礼仪上的清洁(cleanliness),对个人道德关注较少。 神道与佛教: 曾被佛教(“两部神道/Ryobu-Shinto”)吸收近千年。1868 年的革命复兴了神道教,使其成为民族情感的载体。官方将其视为“民族习俗”而非宗教。
日本佛教: 充满活力。
-
净土宗和真宗(Shin
Sect): 最有活力和规模最大的教派。核心是阿弥陀佛(Amida Buddha)的信仰。阿弥陀佛立誓,若不能救赎受苦的人类,祂不接受解脱。真宗强调完全靠信心得救,放弃了苦行和善功(与路德的宗教改革相似)。 - 阿弥陀信仰与基督教: 这种信仰相似性表明人类渴望一种不依赖功德的救赎。然而,佛教的救赎仍是脱离“痛苦、渴望和轮回”,而不是脱离“罪”,因此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
基督教的信息:
- 道德标准: 基督教所强调的诚实和性纯洁是日本所需要的。十字架深化并丰富了日本人自我牺牲的理想。
- 上帝的启示: 神道教和佛教未能将上帝启示给人(日本有“一寸黑暗”的说法)。基督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带来了对一位看不见的父神的坚定信心。
- 救赎与圣洁: 阿弥陀信仰的宽恕成本太低,未能描绘上帝的圣洁。十字架是拯救的信息,它揭示了罪的罪恶性,同时也展示了上帝饶恕的爱。
- 超越民族主义: 基督教将爱国主义置于更广阔的**“上帝的国度”**中。这可以拓宽和净化盲目狭隘的爱国主义。
第七章:基督教:普世宗教 (Christianity the Universal Religion)
本章总结了人类对上帝长久探索的辉煌与辛酸。
非基督教宗教的失败: 尽管这些宗教中有许多虔诚的探求者,但它们未能清楚地揭示上帝的真实本质。它们给出的上帝形象要么是变幻莫测的精灵神,要么是抽象的非人格世界精神,要么是有限的神灵,要么是佛陀对“消除渴望”的呼吁。 缺乏普世性: 只有基督教展现出持续的、坚定的、在所有阶层和种族中规律前进的特质。
基督教的普世性主张:
- 关于上帝的教义: 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和父”**,祂的本质是神圣的爱。
- 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历史存在是确定的。祂不仅用话语,更用祂自己的人格启示了父神。基督教关于上帝的信息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个人——耶稣基督。
- 关于人类的罪: 耶稣基督带来了崇高的道德标准。罪是对上帝的冒犯,是与上帝团契的断裂。十字架的奥秘显示,上帝亲自承担了罪孽,重新恢复了被人类罪恶切断的团契。这种宽恕是“有代价的”,而非“得过且过”的。
- 生命与死亡: 基督徒的生活是与上帝的团契,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内住于人,帮助人克服诱惑,重塑人格。真正的基督教永生希望,源于灵魂在基督里与上帝的本质结合。这种新生命比坟墓更强大。
- 进步性: 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进步的宗教,因为它相信上帝作为圣灵与人交通,使得人们不断学习祂的旨意和道路。
- 简洁与普世: 基督教的信息在于其极端的简洁性,它关注灵魂对上帝的根本态度。它在本质上是普世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种族或阶层。
最终主张: 基督教不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个,而是在其纯粹和完美的意义上,是宗教本身。它回答了人类在不同时代模糊地看到并渴望相信的真理,即上帝对人的自我启示。如果福音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的任务就是世界宣教——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所有,并且必须将宣教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

